这是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刘坚主任在2011年5月22日的讲座中推荐的一篇关于儿童教育的小说。这篇小说,可以引起人们关于基础教育改革的许多思考。
春假的头一天。
我老晚才吃完早饭,正在把钓竿往自行车上绑的时候,妈妈从厨房的窗户里伸出脸来,开始唠叨了:“马上就上六年级了,还这么游手好闲的,你觉得好吗?你看人家正彦!”
我装做没听见。
所说的正彦,是比我小一岁的堂弟。家在同一条街道,又一样是独生子,所以从小就在一起玩。说是一起玩,正彦对我总是惟命是从,好像他是被我牵着团团转似的。
不过,那是正彦每天乘一个小时的电车去市中心的私塾上课之前的事了。
那是一家升学指导有名的私塾,据说光是印好的算数作业一天就有四张。
而正彦照私塾老师说的,全都认真地做完。
加上从去年起,正彦又加入了少年棒球队,私塾放假的星期天又要去练棒球。
“光学习可不行,要稍稍歇口气啊!”说是父母商量的结果,让正彦加入了球队。
这样我们就更加没有见面的时间了。

我把家甩到了身后,立刻就忘记了妈妈的那张阴沉的脸。脑子里,全都被有人从车站对面的河里钓到虾虎鱼的情报占满了。
这是一个晴朗而又暖和的日子。我吹着口哨,瞪着自行车。
我在禁止摩托车和自行车入内的公园的入口停了两妙,朝四周看了看,把自行车骑了进去。
附近没看见警车,那个罗嗦的公园管理员老头今天也没有转来转去。
因为是一条去车站的近道,所以可能的话,最好是从公园里横穿过去,不过没有管理员阻拦,能骑着自行车穿过去的机会是太少了。
上次我成功过一次,那是好几个月前的一个星期日了。那是,我的确是和正彦打了一个照面。
因为要去天文馆,虽说是星期日,我还是起了个大早。骑着自行车从公园里横穿过去的时候,一队穿着少年棒球队制服进行马拉松晨练的队伍与我擦肩而过。正彦也夹在里头。“嗨!”我招呼了一声,正彦的脸上是一种强忍着的、疲惫不堪的表情,冲我回点了一下头,跑了过去。
我用力地踩着脚蹬子,穿过公园,骑进了一条单向行驶的窄窄的小胡同。

一个人影也没有的道路前头,啊呀,站在那里的不是我刚才想起来的正彦吗?到了跟前,我才看出来,正彦正在用烟杂店前头的红色电话机打电话。那里,正好是小胡同和另外一条道路交叉成的三叉路。
从我这边看过去,正彦侧脸握着电话,他没有发现我正在接近。
我把自行车朝正彦的身边靠了过去,我准备哇的一声吓唬他一下。
对着电话说话的正彦的声音,隐约传了过来:“……去玩好吗?”
是在说去玩行吗?怎么这么傻?还真有这样每一件事都要事先请示的家伙哟!
我打算在正彦的背后这样说,笑话他一顿。
我正要去吓唬他,可就在这时,突然从边上的拐角驶进来一辆小汽车。看漏了单向行驶的标志吧?是从禁止入内的相反方向开进来的。
笨蛋!呆子!蠢货!你妈妈凸肚脐!
我在心中骂着车子,皱起鼻尖,冲车子做起了鬼脸。
正在这时,车子突然加快了速度,朝着我和正彦站着的道路就猛冲了过来。
我自己叫了,还是没有叫,记不起来了。不过,那一瞬间我确实是想逃开的。
我丢开了自行车的车把,敏捷地飞到了一边。
可这只不过是我自己的想象而已,实际上我没有飞起来。我脚卡在自行车上跌倒了,被车子撞了出去,飞到了道路的对面。隔着道路的烟杂店的对面,是一家没有患者而倒闭了的牙科医院的空房子,我被摔到了那座空房子的水泥墙上,不省人事了。
我不知道昏迷了多少分钟,苏醒过来的时候,已经是在向医院驶去的救护车里了。
那个开小汽车的,是一个和我妈妈年纪相仿的女人。她说她把车子开进我和正彦站着的道路上,才明白过来方才看到的标志的意思。想把车子停一下,好倒回去,可把刹车和油门给踩错了。
把我撞飞了之后,车子和正彦一同笔直地冲进了烟杂店,和玻璃柜台一起把正彦推到了店里头的墙壁上撞扁了,才总算是停了下来。
据说这些全都登在了报纸上。
我是后来听妈妈讲的。
刹车失灵,把开车的女人吓懵了,说是什么也没有看见。而烟杂店的女主人,偏巧那个时候正在店的后院晒洗好的衣服,没在店里。
烟杂店隔壁的拉面店还没开门,卷帘门还垂在那里。对面,就是刚才说到的那座空房子了。
所以当车子猛冲过来的时候,正彦是怎么个样子,谁也没有看见。
“正彦肯定没有发现汽车!不要说害怕、痛了,恐怕连自己死了都不知道!”
这至少还可以说是一种安慰,这是妈妈的话。
听说那时候,正彦正在给自己家里打电话。接电话的是他妈妈,可不用说,他妈妈当然是什么也没有看见,什么也没有听见了。
这天,虽然是春假的头一天,但正彦的妈妈在往常的同一时间把儿子送了出去。因为上午私塾上课,“新五年级?春季讲习”。
可是,是怎么了呢?正彦的妈妈把上课的时间给弄错了,提前了一天。
正彦也因为被说了一句“春假的课非常重要,可不要迟到啊”,所以连日期也没有确认,就出门去了。
我的伤里头,最严重的是右肩粉碎性骨折。此外一条腿的小腿骨有裂痕,以及东一块西一块的擦伤、划伤,还有就是青肿了。
脑电波也检查过了。
“太好了,没有异常。”
医生这样说的时候,妈妈嚷了起来:“不不,医生。即使是有异常,也不是这次事故引起的,这孩子原本脑子就不好哟!”
右肩动了手术。骨头粘到了一起,我能回家了。
“知道当天没有课,是第二天上,正彦就又坐着电车回来了。于是,就在烟杂店用红色的电话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。”
妈妈在为我做烤肉,她一边切肉一边说。
我右肩的骨头虽然粘到了一起,但为了安全起见,我还是吊起了三角巾,把手腕固定起来了。
烤肉是为了祝贺我出院。
“唉!好不容易私塾不上课,怎么能直接就回家去呢?真是个笨蛋啊!”
“即使是被车给撞了,你的嘴还是那么损!”
“可是,不是白捡了一天吗?如果是换成了我,绝对不会回家的!早就去什么地方玩去了。”
话一出口,我想这下糟了,我偷偷地看着妈妈的脸。
如果是在平时,我是会格外小心的。心里想的事,绝对不会原封不动地哇啦哇啦讲给妈妈听。今天所以没留神,是因为我住了两个星期的医院,感觉迟钝了。
然而,妈妈和往常不一样,不知为什么没有发火。
“可不是嘛,正彦要是到什么地方玩去就好了。只要不在那个地方,不,至少不是在打那个电话,就会发现车子而逃开了吧?那样的话,也许不过就是像你一样,受点伤而已。”
我也没有去多想,那时只是“是啊、是啊”地点了点头。
可是,即使不是背对着车子打电话,正彦就真的能躲开车子吗?即使是早在我被撞飞了之前,正彦就发现了车子,那家伙对于逼近的危险,也许只会发出一声悲鸣,呆呆地直立在那里吧?我这样想,是因为不久之后,就发生了死了的正彦打来电话的怪事。
我一边拼命地往嘴里送妈妈为我切的牛肉,一边说:“离自己家那么近了,他为什么还要特意打电话呢?难道说有什么急事,连六七分钟都等不了吗?”
“是啊,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说是说过平时要是有什么变化或是为难的事时,给家里打电话,会不会是回到家附近了,突然想了起来,慌忙打电话呢?因为是个听话的孩子,打电话只是说私塾不上课。”
“讲习是明天开始,我今天干什么呢?”
说正彦这样问道。
“要做的事情不是很多嘛!算数的预习呀、汉字的默写练习呀。”正彦的妈妈接着就一边笑,一边这样补充说,“那样的话,今天就索性不用学习了,去玩一天也行啊!”
我说:“嗯,那天确实很暖和啊。”
“哎?你说什么?”
“伯母竟会开玩笑,这可不是一般的小事啊。肯定是因为太暖和了,脑子不正常了。”
“那之后立刻就发生了事故。”
据正彦的妈妈说,电话的那一头传来了一声巨响,随后就是一片寂静。任正彦的妈妈怎么“喂喂”地呼唤,也没有人回声了。
听到事故那可怕的声音,隔壁拉面店的老爷子冲了出来,他在被撞得一塌糊涂的烟杂店的前面,看见那部被扯断了电线的红色电话不知为什么一点伤痕都没有,孤零零地滚到了一边。
“那么老实的一个乖孩子!”
妈妈叹了一口气。
我没吭声,闭嘴嚼着肉。
“死了的正彦来电话了。”
那次交通事故过去两个多月的时候,我们听说正彦妈妈因精神受到刺激而失去了理智,竟说出这样的话来了。
我老早就摘下了三角巾,健康地上学去了,正彦的爸爸也恢复到了以前的忙碌的生活当中。
可是,惟有正彦的妈妈(相当于我的伯母),整天缩在家里。
五月中旬的一个星期日。早饭后,伯父和伯母正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的时候,电话响了起来。
“喂,谁啊?听不大清楚。谁?喂喂!”
是伯母接的电话,连问了好几遍对方的名字,冷不防啊地叫了一声,失去知觉倒了下来。
伯父吓坏了,抱住伯母不停地摇晃,伯母总算是睁开了眼睛,说:“是正彦啊。正彦打电话来了啊。”
伯父说:“误会了吧!把别的什么人的声音听错了吧?”可不管伯父怎么说,伯母就是一句话:“不,确实是正彦。”
第二天,伯父趁爸爸中午休息的工夫,把爸爸叫到了公司附近的咖啡店里。这样,我们才知道伯母陷入了这么一种状态。
“这就叫幻听。总是关在家里想着正彦的事,就觉得彷佛能听到正彦的声音了。”
妈妈故意装出一副什么都懂的面孔,说。
第二天,妈妈去安慰伯母了。自从正彦死了以后,伯父他们一次也没有来过我们家,我们也没有去拜访过他们家,一直是这种状态。
妈妈曾经说过:“对方一看到你,就会悲痛欲绝地想到正彦,而我们这边又没有办法来安慰他们。”
妈妈极力坚持说是幻听。到了最后,说得连伯母自己也说:“肯定是我的幻听了。”伯母像是安定下来了,伯父再也没有联系过我们。
我们开始忘记电话的事了。
过去了两个星期。中午休息时,爸爸又被伯父叫了出去。
说是前一天星期日的上午,正彦又来电话了。伯父把邮件投进附近的邮筒里,回到家里一看,伯母脸色铁青地握着电话,两眼发呆地坐在那里。接着,她告诉伯父说:“是正彦来的电话。”伯父从伯母手里接过电话贴到了耳朵上,电话断了。
“知不知道好医生?”伯父对爸爸说。
再怎么说是幻听,到了第二次,伯父觉得都不能置之不理了。伯母的脑子好像是有点混乱了,对于这一点,爸爸和伯父都是持相同的意见,妈妈也是一样。
“也不是没有道理啊。把孩子给逼死了嘛!不论是谁也得受刺激啊。”
我父母因为没有精神科医生的朋友,没能介绍成,一个星期又过去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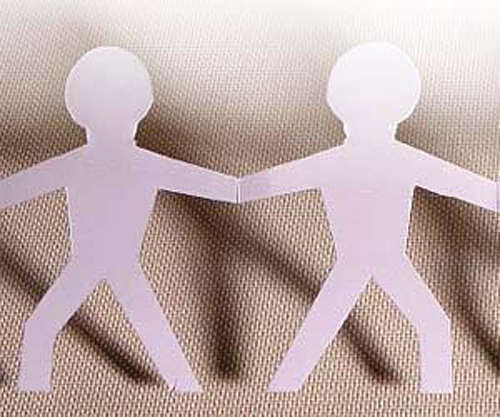
接下来的那个星期的星期一。傍晚,爸爸阴沉着脸从单位回来了。
他说,这回连伯父也接到正彦的电话了。
仍然还是星期日的早上。电话响了,伯母要去接,但被伯父制止住了,伯父拿起了电话。
“说是接着就传来了正彦的声音。”
爸爸皱着眉头,把中午休息时从伯父那里听来的话说了。
“这下可坏了,必须赶紧领两个人去医院!”
“不是那么回事哟!大哥虽然说‘没错,绝对是正彦的声音’,但没像大嫂那样,说打电话来的是死了的正彦……嗯,怎么说呢,也就是说,你不觉得是‘什么’吗?”
爸爸像是说不出口了。
“‘什么’,指的是幽灵吗?”
我把爸爸避开的话,直接了当地说了出来。
“别说蠢话!哪来的什么幽灵?”
妈妈责备我道。
“是呀,哪有那种东西啊!大哥也不相信有什么幽灵!”
爸爸痛苦地说。
“那么,大哥说听到了正彦的声音,是怎么一回事呢?”
伯父说是恶作剧电话。
“正彦活着的时候,在什么地方录过一盘磁带,肯定是有人用它来恶作剧!”伯父是这样想的。
“是这样啊,也许是这么回事。死了的人,是不可能打来电话的啊!——不过,如果是恶作剧的话,这恶作剧也太过分了啊。人家死了孩子,本来就够痛苦的了,怎么还会有人搞这种残忍的恶作剧?要是被我找到了,我非拿竹扫帚抽他不可!”
妈妈已经是怒气冲天了。
爸爸困窘地沉默了一会儿,终于低声问道:“我们家里有正彦声音的磁带吗?”
“你是什么意思?”
“没什么,那个……以前正彦来玩的时候闹着玩灌过一盘磁带,不知还在不在了?”
“大哥不会是怀疑我们吧?”
妈妈张大了嘴巴。
“那是当然了。大哥说如果要有磁带的话,首先就是你们那里。我发火了,他怎么能怀疑他的亲弟弟的家人呢?”
爸爸没有自信地朝我瞥了一眼。顺着爸爸的视线,妈妈也朝我看来。然后,突然就叫了起来:“看你这孩子,都干了些什么呀!差一点儿死了,我还以为从那以后你就变好了呢?
打心眼儿里感到高兴。可你……妈妈可真可怜啊!”
妈妈伸手过来就要拧我的耳朵,我飞快地躲开了,我慌忙叫了起来:“不是我!不要开玩笑啊!我没干那种事!”
可能是我认真了吧?妈妈把手缩了回去,但脸上还是一副半信半疑的表情,直勾勾地瞅着我。
“真的没干吗?”
“是真的哟!太过分了!连自己的儿子你都不相信了吗?”
“你平时就是那样。”
“可这次不同啊。这次的事,绝对不是我干的!”

下一个星期日,那个电话又来了。
就算是恶作剧,也渐渐地变得难缠起来了。
最初,就是伯母失去知觉那回,电话就来过一次。伯父听出来是正彦的声音那回,隔了三十分钟,来了三次。与头一次伯母发觉的正彦的声音不同,一开始伯父还以为是什么地方的孩子打错了,所以是伯父这头把电话挂断了。过了三十分钟,第二个电话来的时候,伯父听出来是正彦的声音
伯父生气了:“适可而止吧!”就把电话挂掉了,那天就那样结束了。
正彦反复在说什么?爸爸问是问了,伯父没有告诉爸爸。
“可是说昨天,从上午就开始一遍又一遍地打来了。而且放下电话,不到十分钟铃声就又响了。”
爸爸把从伯父那里听来的话,讲给了我和妈妈。
“这幽灵可够急的!”
我的笑话没有达到效果。父母连笑都没有笑。
“不过说一到中午,就停止了。”
电话只是在休息天的上午才有,这就越发像是小孩子的勾当了。伯父这样说。
其他的日子,小孩子必须去上学,没有闲工夫打恶作剧电话。伯父还说。
“大多数的大人不也是一样,只有星期日才有空儿吗?”
我提出了异议。
“那么说,一到中午电话就停止了,是去吃午饭了吗?即使休息天也想着要按时吃午饭,吃午饭的时候就不想打电话了,这也只有小孩子才干得出来。是的,伯父就是这么说的。”
“这想得也太过分了,这个星期日,这孩子没给谁打过电话。我作为母亲可以保证。”
妈妈气冲冲地用郑重其事的口吻说。因为伯父怀疑到了我头上,这让妈妈生气了。她自己不是也曾怀疑过我吗?佯装忘记了。
“如果像伯父说的那样是磁带,正彦都录了些什么话呢?”
“今天我终于问出来了。正彦说的是:‘去玩好呢?’其他的什么也没有说。”
我的脑子里,有什么东西卡住了,但我想不起来那是什么了。
我们三个人不过是沉默了两三秒钟。
“你看,不就是像我说的那样,大哥也好,大嫂也好,果然都得了神经病啊!反正就是那么短短的一生,为什么不让孩子开心地去玩呢?那两个人呀,一定是后悔死了。因为害怕正彦是不是会怀恨在心变成幽灵出来,才听到声音的啊。”
妈妈声音大得似乎忘记她说过与正彦比起来,我玩得太过头了的话了。
那之后的两个星期日,伯父和伯母都被劝说出了门。是爸爸劝他们这样做的。爸爸也还是认为是谁在不怀好意地恶作剧。如果一直没有人接电话,那人也就厌倦了,不打了,这是爸爸的计划。
但是,接下来的星期日,伯父一在家,那个电话又打来了。
暑假快要到了。
一个太阳狠毒的星期日的早上。明明是爸爸自己要去伯父家,却把我和妈妈也带去了。
大概是今天也会有让伯父他们痛苦的电话吧!如果像伯父说的那样,对方是个小孩子的话,那要是放暑假了,也许每天都会打过来。
爸爸替伯父去找警察谈过了,警察说为了追查作案的人而使用逆向探知的方法太麻烦,也太复杂了。还不如向电话局申请换一个电话号码,警察建议说。
但是,伯父因为工作的关系,家里的电话特别多,所以如果可能的话,他不想把这个那么多人都知道的电话号码换掉。
“今天一定要想个办法了。要好好地教训这个淘气鬼一顿。可能稍稍吓唬他一下,他就再也不敢了。”
爸爸干劲十足。
连我和妈妈都一齐来,是因为妈妈坚持说要这样做。
“那样当场不就可以证明我们家的孩子不是作案人了吗?”
我好久没有见到伯父他们了。正彦举行葬礼时,我还躺在医院的床上,没能参加。
不过才几个月,伯父和伯母看上去突然老了许多。
家里看上去也让人感觉像是一座不要了的空房子似的。树篱笆的树枝乱七八糟地疯长,玻璃窗模糊不清,钢琴上落满了灰尘。伯母以前是一个那么喜欢打扫卫生的人,“太脏了”是她的口头禅。
伯母端过来的红茶是微温的。伯母自己一口也不喝,只是用匙子不停地搅拌着。即使是妈妈搭话,也是心不在焉,不住地东张西望。
伯父也是一样。虽然是在和爸爸东拉西扯,但我看得出来,他紧张得要命。
房间角落里的电话响了。
伯母吓了一跳,拿着匙子的手僵在了那里。伯父坐不住了。爸爸站了起来,拿起了电话。
“不要再恶作剧了!耍弄大人,是要吃苦头的,懂了吗?”
爸爸平静地说完,挂上了电话。
爸爸冲伯父和伯母点了点头。
“要是再打过来,下回我就不客气了。”
谁也没有说话。过了一会儿,电话又响了。
“混蛋!你就不能适可而止吗?你听好了,我们会请警察逆向探知逮捕你的,懂了吗?”
爸爸狠狠地斥责了一顿之后,猛地放下了电话。爸爸耍了一个花招,脸上掠过一丝得意的微笑。
“被我臭骂了一顿,这下不敢再打过来了。要是再打过来的话,那就只好改电话号码了……”
爸爸还没有说完,电话就开始响了起来。爸爸怒视着电话,这回却犹豫着没有伸手。
伯母突然把匙子往地上一摔,拍起自己的椅子扶手来了:“正彦啊,妈妈也想让你去玩的啊!可都是为了你呀!”
伯母的眼睛向上挑着,声音已经近似悲鸣了。伯父抓住了伯母的手腕,不让她再拍椅子。
“别说了!你再那么胡说,他就更觉得有趣,更恶作剧了。闭上嘴,坚强起来!”
伯母的声音变成了抽抽哒哒的哭泣声。
爸爸和妈妈面面相觑,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。
我下意识地数着电话的铃声:……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…
我忍不住了,走上前去拿起了电话。
小声在说着什么,我听不清楚。
声音十分微弱,让人觉得彷佛是从地球的另一边,不,比那还要远,是从另外一个星球打过来似的。
不过,我终于听清楚说的是什么了。遥远的声音在重复问着一个同样的问题:“……我怎么去玩好呢?”
我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毫无疑问是正彦的声音。是走投无路的正彦的声音。
正彦又一次问道:“……我怎么去玩好呢?”
我突然恍然大悟了。
当爸爸把恶作剧电话的内容告诉了我的时候,好像模模糊糊地想起来了什么,却又想不清楚,到底是什么呢?现在,我清楚地知道了。
电话里问的,与事故之前我偶然听到的,是一样的话。我那个时候听到的,是正彦说的话的结束的部分。不过正彦说的什么,我已经全都忘光了,也许是脑袋被撞坏了的关系吧?
这不是录音带。
是这样啊,那时候我误会了。我还以为正彦是在向他妈妈要求他去玩行吗,把伯母的玩笑当真了,想照妈妈说的去玩,所以才会问怎么去玩好呢。
伯母也理解错了,以为正彦在恨她。
错了。正彦只不过是在寻找因为事故而没有听到的回答。
我,我只不过是凭直觉这样认为。
从电话那头,又传来了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正彦的求助声:“……我怎么去玩好呢?”
正彦这个傻瓜!一直到死,都不知道该干什么,真是一个可怜的家伙啊!
不过,只要没有人下命令,正彦肯定会把电话一直打下去。
“去找伙伴!”
我一边抽噎,一边叫道。
“找到伙伴、去玩足球,去玩骑马大战,不管玩什么都行。”
电话里传来了对方轻轻地搁下电话的声音。
我的眼睛含满了泪水,在刺眼的阳光的照射下,窗外杂草丛生的院子看上去就犹如梦境中的风采。
“怎么了?是谁?不是恶作剧?是你认识的孩子吗?”
妈妈摇晃着我的肩膀,我回过神来。我手里还拿着电话,腿哆嗦起来了。
“啊啊,是一个认识的家伙啊!”
我用攅着的拳头,擦了一把脸,朝伯父和伯母那边转了过去:“放心吧,我想不会再来电话了。我已经回答过他了。”
那以后,电话再也没有响过。